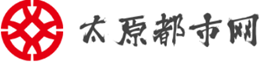近来,民间投资增速断崖式下滑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6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上月开展的民间投资政策落实专项督查工作的汇报。这既表明了中央政府对此问题高度重视,也反映了情势之急迫。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逐月放缓。前五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3.9%,大幅低于2015年全年10.1%的增幅。民间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下降至62.0%,比去年同期降低3.4个百分点。针对严峻形势,一些政策措施已陆续出台:6月中旬,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各省级政府及所属部门,从2016年7月起,在有关政策措施制定过程中实行公平竞争审查;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推动大型商业银行扩大服务中小企业业务,进一步放开基础电信运营、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进一步放开民用机场等领域。 这些措施对缓解民间投资困境无疑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须击中问题的要害。应该承认,前期出台的某些政策,看似为民间资本松了绑,实则在一些领域,制约民间投资的限制条件并未取消;即便这些并未触及根本的政策,也遇到了落实难的老问题。 中国经济能有今日成就,深深得益于放活民间投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民间投资竟渐渐成了一个问题,中央政府为解决此问题付出了努力。新旧“非公经济36条”便是典型。地方上各种细则、配套措施更如过江之鲫。然而,不少政策止步于“文牍旅行”,民间投资环境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显然,民间投资的制约因素已长期存在,并不能完全解释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的剧烈下滑。研究者做出多种解释,包括2015年以来股市、期货市场一度火爆导致民间资金被显著分流,导致“脱实向虚”;此前为获得税收返还等激励,民间投资有数据虚报现象,“营改增”试点全面推进,使这一机制不复存在;新上项目不再有税收优惠,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等等。这些因素是否对民间投资产生影响,影响多大,尚不可确知。但可以说,在L型的经济运行走势下,包括民间投资制约因素在内的结构性矛盾变得空前突出。更可确定的是,前期稳增长政策中,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压过了“牵引效应”。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往往是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时期,2007年初和2008年底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均曾出现民间投资下滑而政府投资上升的情形;不同的是,前两次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民间投资增速在三个月内迅速回升,而此次二者背离更巨、持续更久,迄今看不到改善的迹象。 与前两次制造业投资回报率尚可不同,目前,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利润普遍偏薄。在回报率较高的部门,民间投资或存在进入壁垒,或因融资成本远高于政府投资而被挤出。民企对政府“与民争利”的抱怨更为强烈。2015年以来,政府稳增长采取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和发行的专项金融债都起到了不利影响。PPP的社会资本主要集中在各类国企,专项金融债不仅利率远低于市场水平,而且加剧了挤出效应;有的项目申请到这部分资金后,竟然连PPP模式都抛弃了。这种结果自然有背政府初衷,但对其消极效果应当正视。 可以说,民间投资是中国经济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部分。要真正提振民间投资,需要为其提供市场化的环境。 首先,要改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过低的现状。这需要化解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痛苦,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忍得一时之痛,方能迎来风雨后的彩虹。这就要求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坚定不移地把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 其次,要开放市场准入,实现公平竞争。既要打破存在已久的“玻璃门”“弹簧门”,更要解决根本无门而入的问题。让民企和国企在融资上获得同等待遇,也需要专项检查、指标杠杠之外的新举措。这不仅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打破侵蚀社会福利的垄断,也需要国有企业加快实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战略性退出。 再次,创造可预期的宏观环境也是稳定民间投资所必需。宏观政策最忌信号摇摆,这将导致企业预期不稳,企业家无所适从。其实,只要政府清晰阐述政策目标和规则,民间投资自会基于经济理性,做出选择。 根本而言,投资领域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是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它将进一步推高投资、特别是低效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使卫生和社会工作等社会缺口较大的公共服务业迟迟得不到扩张。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民营经济的意义已无需赘述,关键是使不可操作的政策可操作,可操作的政策快落地。
提振民间投资政策须落地
特别声明: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造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